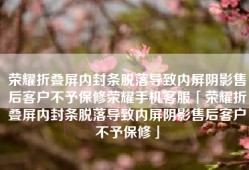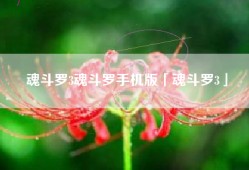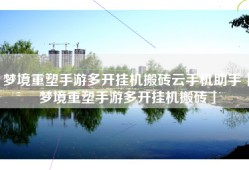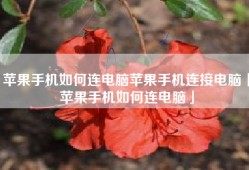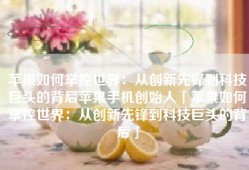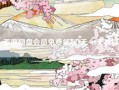最高法何帆谈修订指标体系:不对法院排名,从机制上消除“内卷”
- 资讯
- 2025-01-03
-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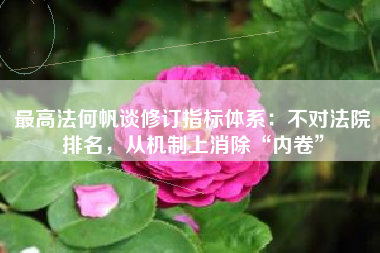
最高人民法院。(图片来源:中国法院网)
“决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立案难’隐性存在。”2024年10月8日,国庆节后上班首日,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在参加司法审判数据会商时强调。
这次数据会商,使用了新修订的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年初适用的26项指标被精简为18项,法官人均结案数、延长审限率、裁定再审率、司法建议反馈率等指标被取消。值得注意的是,指标的运用机制也作了调整,相关数据主要供研判、分析使用,不得通报排名,不能额外加码,一些“达标线”也适当下调,可以有效遏制拖延立案等“反管理”行为。
过去,一提到指标,常见的担忧是,会不会出现“唯数据论”倾向?向排名看齐,会进一步加重基层负担。那么,最高法为何要设置指标体系?具体运行成效如何?这次修订能否达到为基层减负的效果?针对上述话题,南方周末记者对话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何帆。
比方说,法院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但是,这个“感受”如何量化评价呢?全国有三千五百多家法院、每年有四千多万案件,群众对立案、调解、审理、执行的过程、结果是否满意,意见集中在哪个条线、哪个地区、哪个环节,不可能依托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全面了解。比较科学、公允的办法,是围绕人民群众对案件质量、效率、效果的核心诉求,设置案-件比、超12个月未结案件比、执行到位率等指标,用以统计、发现、检视和改进我们工作中的不足。
所以,指标只是一个中性、客观的测量工具。问题的核心不是该不该设指标,而在于指标设置是否合理、运用是否科学,以及能否实事求是地看待指标。好的指标体系,一定是个有机联系、相互支撑的“评价系统”,既能全面展示问题、符合审判实际,又遵循司法规律、不强人所难,让被评价者心服口服。
比如,一些法院把结案率作为评价办案效率的常用指标。简单讲,就是看一个统计周期内法院收了多少案件、结了多少案件。起诉时间越是接近考核期末,案件就越不可能在这个周期办结,为避免拉低结案率,有的法院就会拖延立案甚至不立案。
这表明,科学管理离不开一套符合司法规律、较为系统完善的指标来评价审判工作。2023年,我们在制定新的指标体系时,经过反复调研、征求意见,决定充分吸收各地行之有效、认可度高的指标,坚决弃用不科学、不合理的指标。这套指标中最受法官和各界认可的,是用审限内结案率替代了结案率,法官只需按照审限把握办案节奏,就能够有效杜绝“年底不立案”等问题发生。如果有利于实质解纷、案结事了,该延长审限就依法延长,这样就彻底打消了法官的内心顾虑。
总体而言,指标体系以案-件比为核心指标,同时按案件质量、效率、效果三个层面,分别设置了对应的指标项。案件质量类包括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等;案件效率类包括审限内结案率、超12个月未结案件比等;案件效果类包括诉前调解成功分流率、调解率、执行到位率等。
创设案-件比指标,就是要引导各级法院将重心从“案件结没结”转向“矛盾解没解”,注重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力争把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环节做到极致,更快更好地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当然,每个诉讼都有它的具体情况、每个当事人也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和诉讼权利,案-件比作为综合指标,需要与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对照分析,不适合直接套用于某一层级、某一个法院。
南方周末:这些指标会计算总分吗?有没有一票否决性质的指标?
何 帆:指标体系没有赋权总分,也不存在任何一票否决的指标。总分制的弊端在于,会掩盖单项指标本该反映出的问题,还会导致大家只关注高分值指标、舍弃低分值指标,把抓工作变成了权衡利弊的“算数游戏”。
举个例子,空气质量指数就是把空气中的各种成分按不同权重算出的数值,可以反映空气污染情况,但它很难反映具体是哪种成分导致的污染。比如,两个地方的空气质量指数一样,一个可能是因为 PM2.5 高,一个可能是臭氧含量高,存在的问题不一样,需要针对性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指标体系是一个整体,但单个指标的情况,也有必要逐项分析,下足“绣花功夫”。
从数据上看,指标体系施行一年多来,案-件比持续下降,执行完毕率、执行到位率显著增长,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等指标明显趋优,一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大幅下降。这些都充分说明,按照指标体系确定的价值导向,把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做优、把法官的司法责任压实,以人民为中心才可能做实,老百姓的司法获得感才会提升。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何帆。(图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正向的压力可以转化为提升的动力,关键是遵循司法规律。如果把抓工作等同于抓指标,“质效不够,指标来凑”,或者用层层加码、张榜公示等方式“制造压力”,当然是不对的,甚至事与愿违。但是,指标的作用是对照分析、检视不足,不是无限追高,如果通过指标发现案件质量、效率、效果存在不足,相关法院、法官当然会有压力,就得促进责任落实,进一步抓实审判管理。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在发展,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也在变化。与之相比,我们的审判工作,还有许多跟不上、不适应的地方。在审判工作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落实落细司法责任制的大背景下,如果审判质效改进还不明显,离当事人的期盼还有距离,期望在“宽松软”的管理模式下继续“躺平”,更是不可取的。
各地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都“原汁原味”地梳理分析,作为本次修订的决策素材。从调研情况看,绝大多数法院人员认为,审判工作不能各行其是,抓工作不能光靠自觉自律,遵循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必须有,这也让我们感到很欣慰。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个别二审、再审法院因顾忌本辖区质效数据,片面追求绝对的“低改发率”,对原审裁判能改判、发回重审的,都直接维持,导致“改发率”指标被人为异化。这种行为美化了数据,但无疑会损害司法公信。从司法规律看,案件该维持、改判还是发回重审,必须结合个案情况具体分析,不宜预设立场,更不能为“追高”或“压低”数据影响审判组织的判断。
本次修订用“改-发比”取代了“改发率”。所谓“改-发比”,就是将评价对象从“改发率”关注的被上级法院改判、发回重审案件占原审案件的比例,调整为改判、发回重审案件之间的比例,引导二审、再审法院在纠偏纠错时,树立“当改则改、慎重发回、定分止争”的工作理念,尽可能依法直接改判,减少不必要甚至不负责任的发回重审,防止程序空转。从“率”到“比”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体现的却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维护的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例如,一个地区的二审案件“改-发比”是1:0.2,另一个地区是1:0.1,意味着在对待存在问题的一审裁判时,后者比前者更多采用改判而不是发回重审的方式结案,这是符合科学管理要求、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另外,我们还对一些指标的合理区间作了调整,确保相关法院“踮踮脚”“努努力”就能做实公正、高效审判执行工作。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法院为了追求诉前调解成功分流率和诉前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达标”,存在在诉前阶段强推调解、不及时立案的现象。对这两个指标设置更趋合理的区间参考值,有利于下级法院实事求是开展好诉前调解工作,调解不成的及时立案,做实“能调则调、当立则立”。此外,平均结案时间的区间也作了调整,更加考虑目前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把公正审理案件放在第一位。
为了引导各地各级法院将指标数据作为掌握、分析审判运行态势的依据,我们建立了合理区间机制,受到大家的认可。如果说指标体系是检视审判执行工作成效的“体检表”,合理区间就是判断相关工作是否“健康”运行的“参考范围”。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血压高过了参考范围,这时候就应该看看问题出在哪儿,然后对症下药、调理身体,而不能还是我行我素,多躺平、不运动,那就会出大问题。反之,凡是进入合理区间的,即可视为符合要求,不需要再分三六九等,也不宜脱离实际盲目追高。
本次修订中,我们重申了指标体系的“体检表”定位,突出“重视区间、杜绝排名”的工作导向,让各级法院放下“唯数据论”的思维定式,不以排名比高低、要以实绩论英雄,从机制上消除“内卷”冲动,真正不为名次所累。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将加大对数据真实性和办案规范性的核查检查力度,及时发现、严肃查处、坚决纠正数据造假、注水等行为。
南方周末:传统印象里,指标应该是越优越好,为什么还要设置“封顶线”?
何 帆:办案要综合考虑国家、社会、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依法作出裁判,指标也不是所谓“越优”越好。不设“封顶线”,地方法院就有无限追高、追低的动力,甚至脱离司法规律搞数据“跃进”。比如,案件情况是复杂的,总有一些不可控的客观原因影响审理进程,追求100%的审限内结案率,就违背了司法规律。
所以,最高法对于地方法院异常突出、跳跃进步的指标值,非但不鼓励,反而要加大检查评查力度,看看是否存在注水、造假的问题。
除此之外,最高法内部还将指标数据作为工作秘密管理,各高级法院只能看到自己辖区的数据。同时,我们还要求高级法院在适用指标体系过程中,尊重实际,为中级、基层法院改进审判工作留有必要的时间空间,不得高强度、高频次地开展通报考评调度,或者脱离实际搞任务摊派、定额定标,避免引发迫于压力的“数据冲动”。
2024年3月1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人民视觉供图)
从评价内容看,由18项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这“一把尺子”是够用、管用的,也能防止各地再额外增设不必要、不适当的指标。但是,在运用过程中,就要考虑地域、发展水平等不同情况,尽力做到量体裁衣、做实量力而行。实事求是,会促进每一个法院认同评价结果,更有动力去改进工作。
其二,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法院设置不同的“达标线”,让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都有符合自身实际的提升空间。
其三,不做无意义、不切实际的“攀比”,鼓励、引领每个法院和自己比、和上一年同期比、和工作改进前比,循序渐进,不断提升审判质效。
指标体系是抓主要、管重点的,不宜追求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本次修订的一个突出导向,就是将指标体系在地方法院的具体实施责任压实到高级法院,督促其因地制宜、担当作为。考虑到差异化评价的问题较复杂,我们认为,最高法总体上应把准方向、抓好宏观,在此基础上要求各高级法院综合考虑收结案数量、人均结案数量、案件结构、队伍素质等因素,完善、用好本辖区不同法院的差异化评价标准。据了解,有些高级法院较早地开展了差异化评价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浙江法院按照法官人均结案数量,将地区、中级和基层法院划分为三组,对效率指标设定不同区间参考值。这些有益尝试,都会成为未来最高法制定全国方案的借鉴经验。
需要强调的是,差异化评价必须是建立在共性基础上的差异化,主要体现在合理区间参考值和评价结果的变通运用上,而不是另起炉灶、单搞一套。根本是必须遵循司法规律,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审判工作情况不断优化调整、改进完善,使评价结果更有可比性、更加公平合理,更能清晰研判出不同地区、层级法院的工作实绩。
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站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站将会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E-mail:xinmeigg88@163.com
本文链接:http://www.bhha.com.cn/news/5078.html